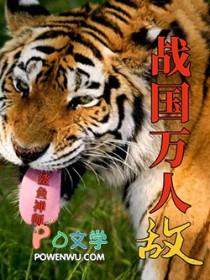爪机书屋>不完美的协奏曲 > 第8章 附幕三 醉里孤灯辉耀月(第4页)
第8章 附幕三 醉里孤灯辉耀月(第4页)
混乱的思绪无法理清。
酒精让我的大脑放弃了深究,只剩下最直接的感觉。
我靠着的这个后背,宽阔,平稳,虽然抱怨着“好重”,但托着我的手臂很有力,一步一步走得很稳。
夜风吹过我们,带来凉意,但贴着的这片温热,驱散了那点寒冷。
一种奇异的安心感,混杂在眩晕和燥热里,悄然滋生。
“才不重…”我无意识地出几个含糊的音节,脑袋在那片温热的布料上蹭了蹭,想找一个更舒服的位置。
背着我的人似乎僵了一瞬,呼吸屏住了片刻,然后叹了口气,继续往前走。
安静。只有规律的脚步声,远处隐约的车声,还有风声。
在这片包裹着我们的安静里,一些平时绝不会说出口的话,失去了逻辑和理智的管辖,顺着滚烫的血液,从心口最直接的地方,涌到了喉咙口。
“藤原…同学。”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,语很慢,吐字大概也有些模糊。
“…嗯?”背上的人应了一声,声音依旧带着疲惫。
“谢谢你…”我闭着眼,靠在她肩胛骨的位置,感受着那里随着呼吸的起伏,“送我回来…”
她没有说话,只是脚步似乎放得更慢了些。
头脑依然有些昏沉,热的感觉让我不再思考,生物的本能绕过了我所有精心构筑的的壁垒,让里面那些最原始,最未经修饰的感受,毫无阻碍地流淌出来。
我必须说出来,那些她应该听到的东西。
“藤原同学…真的,很厉害呀。”我缓缓地说,每个字都像是从一团温暖的棉花里费力拽出来的,但说出来后,却有种奇异的顺畅感。
背着我的人,呼吸似乎又顿了一下。
“面试的时候…你一开始,就想把大家,都组织起来。”我的思绪飘回那个灯光刺眼的多功能教室,飘回我们围坐在一起、气氛紧张的讨论,“虽然…方法不够…不够好…但换我来我肯定…做不到的…”
我想起她快分配角色时的果断,想起她表达策略时的强硬。
那不是出于恶意或单纯的掌控欲,我能感觉到那下面,是一种急于想把事情做好,想带领团队走向成功的迫切。
“那种…想要负责,想要把事情做好的心情…我……感觉得到…”我喃喃,酒精让我失去了斟酌词句的能力,我只感到身前的热量,让我想要去说些什么,让我安心,让我想把自己所有的思念,全都倾吐出去。
“克洛伊…唱歌的时候…你也很着急吧?但你稳住了…后来,还帮清水解围…”
这些都是我看到的,认真,负责,即使在压力下也不轻易放弃对局面的努力。这才是藤原同学呀。
“你很认真。”我把脸颊更紧地贴着她的背,仿佛这样能传递我的意思,“对戏剧,对团队,甚至对数学…”
她又颤抖了一下。
“都很认真…那种…不服输的劲头…”
我伸出手,指尖轻轻碰了碰她手臂的衣料。触感微凉,但下面的手臂肌肉因为承重而绷紧着。
“我…”我停顿了很久,像是在积攒力气,也像是在辨认自己心底最真实的那个声音,“其实…有点羡慕呢,藤原同学…”
羡慕你能那么直接地去争,去表达“我想要去做”,去承担“我应该负责”的重量。
羡慕你身上那种,即使受挫,也依旧挺直背脊,不肯熄灭的倔强火光。
那是我缩在自己的壳子里,用分析和计算小心翼翼保护起来的东西。
背着我的的人,彻底沉默了。
连脚步声都放得更轻,仿佛怕惊扰了什么。
只有她的心跳声,透过相贴的背脊,一下,又一下,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,比刚才快了些。
夜风好像也更凉了,吹在我烫的脸上,稍微缓解了那恼人的燥热。
街道很安静,两旁的住宅楼里,星星点点的灯火透出窗子,像落在地上的安静的星星。
我们就这样,在寂静的夜色里,缓慢地前行。
我趴在她背上,意识在清醒和混沌的边缘浮沉,那些藏在心底最深处的话,像打开了闸门的溪流,不受控制地继续流淌。
“我呀,总是…想了太多。”我低声说,带着自嘲,“风险,成功率,还有…会不会给别人添麻烦。所以我总是缩在后面。就算站出来…也是什么都想好了之后…但那肯定…是来不及的。”
我羡慕你的勇敢。
羡慕你敢直接去争那个主持的位置,敢在情况不利时还试图掌控节奏,敢在落选后…依然用那种挺直背脊,不肯露出狼狈的姿态,走出教室。
“我知道…那不容易。”我的声音更低了,几乎像是在耳语,但我知道她能听见,“我可以理解那种…明明很努力了,却因为方式不够讨巧,或者…不够灵活,而得不到认可的感觉。”
就像她在面试中,试图用强势的框架整合团队,却被我提出的策略无形中取代了核心位置。
她的努力和意图是真实的,如果长期来看,她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,只是在那套即兴的,更看重应变的规则下,显得有些不合时宜。
“我知道那种…不想输…尤其是不想输给自己的感觉。”这句话,更像是我在对自己说。
我清楚,那个在清水唱歌前一刻,因为过度思虑而大脑空白,几乎要搞砸一切的自己,才是真的输了。
我说着这些话,眼泪不知道为什么,毫无预兆地就涌了上来。
不是因为悲伤,也不是因为委屈,更像是一根长期紧绷的弦,在这意外的坦白中,突然松弛下来后,释放出的混合着无法言说的情绪的的液体。
温热的液体顺着我的脸颊滑落,滴在她肩颈处的衣料上,留下一点深色的湿痕。